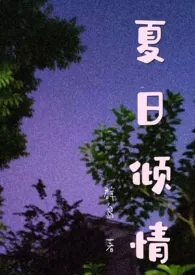高衙内像颗皮球一样跳进来,一脸天真烂漫地叫道:“爹!”
高俅喝道:“孽障!跪!”
高衙内被他吓了一跳,委委屈屈地跪下来,小声道:“我叫声‘爹’又怎么了?你不想听,我不叫还不成……”
“你干的好事!”
高衙内拧着脖子道:“潞王爷家的老三不是我打的!”
“谁问你这个!”
“在翠云楼争风吃醋,打死人也没我的事!都是小梁子他们干的!”
高俅被这个义子气得七窍生烟,指着那把屠龙刀喝道:“我问你!这是怎么回事?”
高衙内抬起头,“你说这个?哈,爹,我还没跟你说呢,孩儿看中威远镖局李总镖头的老婆,想把她弄来玩玩,谁知道她有个妹子比她还漂亮几分。孩儿一打听,哎哟喂!你不知道她妹子竟然是林冲的老婆哎!孩儿想到硬抢,怕往爹的脸上抹黑,于是想了个好主意,把这刀给林冲,然后说府里失窃,把林冲当贼抓起来,然后把他老婆抢过来!爹,孩儿够聪明吧?爹,你还没见过林冲的老婆吧?真是水灵!那腰细的,屁股扭的……等孩儿玩过了,让爹你也玩玩!”
“孽障!胡说些什么!这刀岂是你轻易动的!”
高俅抓起戒尺,喝道:“把手伸出来!”
高衙内把手背到身后,叫道:“你凭什么打我!我拿了你的刀又怎么了!你是我爹!你死了这些东西都是我的!”
“都是我疏于管教,才让你这般胡作非为!”
高俅说着举起戒尺。
高衙内见他真的要打,直接往地上一躺,打滚叫道:“打人了!打人了!我又不是你亲儿子,你凭什么打我啊!娘!娘!没娘的孩子真可怜!要被干爹打死了!啊啊……”
高俅下令杀光所有见过屠龙刀的人,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,称得上杀伐决断,这会儿对着撒泼的干儿子,手里举着戒尺,怎么也打不下去。
忽然啪啪两声脆响,高衙内肥嘟嘟的脸上多了两个掌印。
高衙内的嚎叫声卡在喉咙里,呆呆看着那个脑袋上包着纱布,看起来有点眼熟的男人,半响后惨叫一声:“爹!有人打我!”
说着扑到高俅怀里干嚎起来。
高俅扔下戒尺,顿足道:“打得太轻了些!来人!快拿冰块给衙内敷上!别哭别哭,让为父仔细看看!”
程宗扬哭笑不得,高俅这护犊子也护得太不像话了。
“哭个屁!”
程宗扬喝道:“再哭还要打屁股!”
高衙内的干嚎声立刻一顿,带着三分怯意从高俅的怀里偷看着程宗扬,片刻后忽然叫道:“你!你不是那个……”
“我是高太尉请来的老师,从今往后都由我来管教你!不听话就打,连太尉也不能说个‘不’字!”
高衙内先看高俅,高俅虎着脸点了点头。他又看了程宗扬一眼,然后倒在地一通乱滚。“我不要!我不要!我不要!”
程宗扬朝他屁股上啪啪打了两巴掌,那小家伙捂着屁股跳起来,带着哭腔叫道:“爹!”
高俅冷哼一声:“从今往后便由程先生来教你!敢不听话,小心挨打!”
说罢拂袖而去,将拿来冰块的仆人赶到院外。
高衙内也想跑,却被程宗扬揪着衣领扯回来。“往哪儿跑?”
高衙内大喝一声,摆出拳法的架势,叫道:“看我的降龙三十六掌!”
“啪!”
高衙内刚摆好架势,脸上又挨了一记。
没等高衙内哭出声,程宗扬喝道:“哭一声一记耳光!”
高衙内终于明白爹也靠不住,一手捂着脸,老老实实地闭上嘴。
“这才乖。”
程宗扬道:“认出我了吧?”
高衙内点点头。
“师师姑娘呢?”
高衙内指了指外面,哭丧着脸道:“我、我没碰她……”
“那你太幸运了。”
程宗扬笑眯眯道:“你要敢碰她,我就把你阉了,送你到宫中当太监。”
高衙内咽了口吐沫,被打肿的脸蛋微微发白。
“瞧你那胆量,阉了又有什么?哪天惹得我不高兴,我把你的鸡鸡竖着一切两半,一个变两个,你挺着出去才威风呢。”
高衙内捂着脸,嘴巴一咧,几乎哭出来,“你别吓我……”
“行了小子,往后我就是你的老师,你就叫我师傅吧。”
“师傅……”
“我没听到!”
“师傅!”
“你是属蚊子的吗?”
“师——傅!傅!傅……”
“这才乖嘛。我要去看看师师姑娘,乖徒儿,替为师拿好灯笼!”
高俅身上有太多的秘密,自己在太尉府内住在一处僻静的独院,却把正房让给儿子去住。
高衙内从小被骄纵,养就无法无天的性子,他的年纪不过十几岁,门外却站了一排足足十几个姬妾,一个个花枝招展。
看到高衙内亲自拾着灯笼,小心翼翼陪着一个陌生人过来,那些姬妾不禁面露讶色,但诸女不敢做声,小心屈膝,双手放在身侧,向来人福了一福。
卧室内灯火如昼,宽大的床榻上躺着一个女子,看容貌正是李师师。
她衣衫已被剥去,贴身披着一条艳红的肚兜,掩住胸乳,裸露着雪玉般的玉臂和双腿,一副玉体横陈、任君大嚼的美态。
只是她眼上蒙着一条红绫带,连两只耳孔也被丝巾塞住。
程宗扬朝高衙内脑门上拍了一把,咬牙道:“小崽子!你不是说没碰她吗?这是怎么回事?”
“真没有!”
高衙内叫屈道:“我连根指头都没碰她,只是让人给她换了换衣裳,敢有半个字假话,天打五雷轰啊师傅!”
“你把她剥这么干净,又不碰她,难不成你下面不中用,只拿来看的?”
“是这么回事……”
高衙内贴在程宗扬耳边道:“不瞒师傅说,我把这小婊子的娘弄上手了,那个老骚货浪得很!就这么用了她女儿没什么意思,徒儿想了个主意,把她的头脸耳朵都蒙上,一会儿把她娘叫来,说我新搞了个小婊子,让她娘按着我来开苞。等干过,我再把她头罩解了,嘿嘿……”
“自家生的女儿,阮女侠会认不出来?”
“那骚货眼里只有黄澄澄的金子,给她一个戒指,她哪还会看别的!”
高衙内眉飞色舞地说道:“那骚货真是够味!师傅,你也尝尝?”
“免了吧。”
程宗扬冷笑道:“小崽子,这是你的主意?”
“当然!师傅,这主意好玩吧!”
“是陆谦给你出的吧。”
高衙内讪讪道:“师傅,你怎么会知道?”
“滚!”
“哎!”
高衙内如蒙大赦,转身就走。
灯光下,李师师光洁的玉体散发出如明珠般的肤光。她的皮肤莹白,身材娇小玲珑,整个人如同一只精美的玉坠,让人禁不住想抱在怀中温存。
程宗扬咽了口口水,先拿了锦被将李师师娇美的玉体盖住,然后才解开她的眼罩。
眼罩一松,两行珠泪滚落下来。李师师玉颜凄楚,银牙紧紧咬着红唇,不肯作声。
“是我!”
程宗扬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,得意洋洋地说道:“惊喜吧!我早说过,你是我盘里的菜!除了我,谁也不能动!哈哈!”
李师师却没有露出半点惊喜,她闭着眼,泪珠漱漱而下。
程宗扬一拍脑袋,拍到伤口,先哎哟叫了声痛,接着道:“我忘了,你的耳朵还塞着。”
“不用了。”
李师哽咽道:“她们塞得不紧,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。”
程宗扬愕然间,李师师睁开双眼,泪眼模糊地说道:“我想死……我宁可让那个畜牲占了身子,也好过这样丢脸……呜呜……”
程宗扬的手掌伸入被中,握住她的纤手。李师师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那样紧紧握住,哭得肝肠寸断。
“对不起……我……我曾经想利用你,”
李师师哽咽道:“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……”
程宗扬笑道:“能被师师姑娘利用,是我的荣幸。”
李师师的唇角抽动一下,想笑却没笑出来。
半晌她轻声道:“小时候娘曾经带我去算过命,那个白须飘飘的匡神仙说,我的命是贵人格,十八岁时会有一场大难,而我的命中注定会遇到贵人。”
程宗扬曾听到阮香琳提及此事,没想到她这会儿主动提起。
“如果我选择贵人,虽然会小厄,终究可以遇难成祥,父亲也会因此飞黄腾达。如果错过贵人,不但性命不保,甚至还会祸及父母。这些话娘从小就对我讲过,这次镖局出事,娘认定就是匡神仙说的大难。”
程宗扬玩笑道:“我也算不得什么贵人吧?”
李师师流泪道:“娘说那个贵人是高衙内,整日劝我从了他,好让父母飞黄腾达,不然就是我害了他们。”
“令堂……嘿嘿。”
程宗扬干笑两声,没再说下去。
李师师抬起梨花带雨的娇靥,凄然道:“如果不是你,我这会儿已经蒙受一生一世也无法洗脱的耻辱。我现在才发现,即使有身为总镖头的父亲,有受人尊敬的师门,有一个号称英雄豪杰的姨父,自己却没办法改变什么。”
程宗扬不知道该怎样怎么安慰她,只好道:“别哭了,休息一下。”
“不,我要说!”
李师师咬了咬唇瓣,“他们玩过我娘,又想玩我们母女。太尉府的权势和地位那么大,我逃不了,也躲不开……”
哭泣中,李师师将自己的委屈和遭遇的耻辱一并发泄出来。
程宗扬可以理解,好好一个大姑娘,母亲竟然抛开贞洁和起码的道德,成为临安城臭名昭着的花花太岁又一个玩物。她是一个妻子、一个母亲,却为了钱财和荣华富贵,委身给一个年纪只有她一半的小衙内。
“一想到这样的耻辱,我没有勇气再活下去……”
李师师哽咽道:“我想过去死,我真是太没用了,只有这一件事是我能做到的。”
“别说傻话了。”
程宗扬道:“你才十八岁,对吧?这年纪还不算活过。”
李师师的眼泪仿佛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,她伸出一只雪白而纤柔的玉手,“救我……”
她央求道:“把我从这个噩梦里救出来,好吗?”
程宗扬沉默片刻,然后道:“你能舍弃自己的家人吗?”
李师师毫不犹豫地说道:“我宁愿从来没有出生过。”
“你的师门呢?”
李师师掉着眼泪摇了摇头,显然对师门已经心灰意冷。
“那好,”
程宗扬郑重说道:“我的公司缺少一名公关部经理,我代表盘江程氏,诚挚地邀请师师姑娘加入本公司,担任本公司首任公关部经理。”
“公关……”
李师师的玉颊带着泪珠,愕然睁大眼睛,“这是什么?我可以做吗?”
程宗扬笑了起来。“相信我的预感,你会是第一流的公关人才。”
程宗扬从卧室出来,迎面便是一刀劈下。那汉子生得又粗又壮,两膀似有千斤之力,手中的快刀霍霍生风,但真气驳杂不纯,显然不是什么好手。
程宗扬避开刀锋,向院中看去,只见十几名恶仆持刀挟棒,高衙内一手捂着脸,跳着脚叫道:“打死他!往死里打!出了事本衙内一个人全担着!”
这头小猪仔倒是不蠢,眼看斗不过自己,师傅前、师傅后叫得殷勤,转眼就叫来一帮手下跟自己玩命。
可惜自己今非昔比,想玩命也得有资格。程宗扬有心立威,看那恶汉又一刀劈来,他不闪不避,一拳轰在刀身侧面,真气一吐即收,将那柄钢刀硬生生打得反折过去。
那恶汉虎口震裂,手臂被弯折的刀锋带到,留下一道血淋淋的伤口。
众人惊愕间,程宗扬使出太一经的心法,身如鬼魅,一闪掠到高衙内面前,揪着他的衣领把他拎起来,笑眯眯地道:“乖徒儿,想找为师讨教什么功夫?要不然就是鸡鸡痒了,想一个变两个,一手一个撸着玩?”
高衙内脸色煞白,片刻后无比心虚地说道:“是那个……那个……老骚货来了……徒儿想请师傅去玩……玩……”
“师傅看着你这徒儿肥嘟嘟的又白又嫩,像是很好玩的样子,不如让师傅来玩一个?”
高衙内带着哭腔道:“徒儿一点都不好玩……真的!”
“玩玩才知道嘛。”
程宗扬道:“乖徒儿,把裤子脱了,让为师先给你玩个后门别棍!哟,小崽子,你怎么尿了!”
“徒儿被吓得憋不住……”
“这样也好,先尿净拉空,免得师傅一会儿把你的屎搞出来。”
高衙内叫道:“师傅饶了我吧!我再也不敢了!打死我也不敢了!”
“师师姑娘今晚就住在这里,让那些丫鬟进去伺候,你给我滚得远远的。敢靠近这里半步,我就把这两颗核桃塞到你的鸡鸡里面。”
高衙内一愣,“那怎么塞?”
程宗扬微笑道:“想试试吗?”
高衙内连忙道:“不想不想!”
高俅坐在书房生闷气,见程宗扬进来,摇头道:“我这个孩儿啊……”
程宗扬笑道:“小孩子嘛,必要的时候也该打打。”
程宗扬心里有些奇怪,原本他以为高俅只是仗着自己的地位骄纵儿子,现在看来,高俅对小衙内不是一般的疼爱。
别人看屠龙刀一眼,他就要斩草除根;偷了刀出去胡闹的高衙内,他连打都不舍得打一下。别说干儿子,就是亲儿子,溺爱到他这样也算少见。
高俅叹了口气,似乎不愿多说。
程宗扬坐下来。“高太尉既然是自己人,让小弟解开不少谜团,但还有几件事,请太尉指点。”
高俅拂了拂衣袍,坐直身体:“六朝知我底细的唯你一人,有什么疑惑,尽管问吧。”
“第一件,岳帅是生是死?”
高俅沉默良久。“岳帅那种人岂会轻易死掉?但如果岳帅还在世,这么多年终该有些线索。”
“我明白了。”
程宗扬有些头痛的想:岳鸟人的生死看来还是个谜。
“第二件,岳帅安排太尉进入军界不会只传递一些情报吧?如果有别的用意,太尉能不能告诉我?”
程宗扬解释道:“我准备在临安做些生意,不知道会不会与太尉的目的冲突?”
“岳帅吩咐高某的事,高某每天都在做,临安城中尽人皆知,告诉你又有何妨?”
高俅徐徐道:“你在江州与禁军交过手,觉得上四军如何?”
“装备精良、衣甲鲜明,但徒有其表,与传说中的禁军精锐……”
程宗扬明白过来,拍案道:“原来如此!”
高俅掸了掸衣袖。“这些年禁军表面还有几个名将,但指挥使以下多是趋炎附势之徒,虽然还有上四军的名号,却已今非昔比,军中贪渎之辈横行,所谓精兵不过虚有其表。”
程宗扬在江州就有所怀疑,捧日、龙卫二军名头虽响,实力却远不及自己想象中的强悍。高俅军权在握,这些年来釜底抽薪,等于是抽掉禁军的脊梁骨。
高俅道:“还有什么疑惑,一并说来。”
“确实还有一件。”
程宗扬盯着高俅的眼睛道:“太尉府走失的那个侍妾,究竟是怎么回事?”
高俅道:“你看到我身边有姬妾吗?”
程宗扬一怔,这才意识到院中的蹊跷。高俅并不是什么清官,他掌权这些年大肆贪墨,在享乐上的花费没有半点含糊,室中陈设无一不是精致考究。
但比起高衙内小小年纪就坐拥成群姬妾,高俅这个太尉的身边却显得十分冷清。
“二十余年来,高某每日如履薄冰,从不敢收纳姬妾。”
高俅道:“那个侍妾并不是我府上的。”
“那是谁?”
高俅吐出两个字:“宫中。”
程宗扬震惊之余,只听高俅道:“朝中有贾太师的贾党,有王宰相的王党,还有道门弟子的道流。但谁都知道,我高俅是得幸于先主的幸臣,是货真价实的帝党!陛下有什么不好处置的私事都会找我来做,因此我贪墨这么多年,也无人能动我分毫。”
高俅又道:“陛下生母早亡,幼年继位之后,最亲近的只有一位奶娘,但数个月之前,这位奶娘在宫里突然失踪。事涉宫闱,陛下不好交付有司追查,只好暗地召见于我,让高某查访。”
“太尉为什么放出风声,死活不论呢?”
高俅道:“陛下已过婚龄,至今却未纳后妃。岳帅于我有恩,高某不才,又深受先主信赖,为陛下计较,这位奶娘与其活着,不如一死了之。”
原来梦娘真实的身份是宋主的奶娘。有这么一个活色生香的大美人儿,我要是宋主也对别的女人不感兴趣啊!
高俅苦心孤诣,借着宋主的托付,不惜开罪宋主也要了结这桩丑闻,手段合不合适暂且不论,这分心意也算对得起宋主当年的宠幸了。
只不过梦娘那样一个大美人儿会和宋主那个小崽子有一腿,怎么想都觉得别扭。黑魔海竟能把她从宫中掳走,看来他们的势力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强大。
思索中,高俅道:“你与林冲有些交情?”
程宗扬道:“有一点。”
“当日你在情报里让我调查林冲,我以为他给你们惹了什么麻烦,正好犬子闹出这档事,准备借机除掉他。既然如此,便把他放了吧。”
“这倒不用。”
程宗扬一边消化高梂吐露的秘闻,一边道:“林教头这边倒要请太尉帮忙……”
高俅听了片刻,点头道:“此事不过举手之劳!”
秦桧讶道:“刺配筠州?”
程宗扬道:“死罪可免,活罪难饶。林教头再怎么样也是执刀进了白虎堂,能保住命就不错了。”
秦桧沉吟半晌,“如此也好,只是高衙内那边未必肯罢手。”
高俅的身份属于绝密,他已经潜伏二、三十年,总不能自己一知道就大嘴巴地满世界乱说。如果不出意外,程宗扬打算这辈子都把这事烂在肚子里。
从太尉府离开时,程宗扬把李师师留在府中,委托高俅照顾。眼下司营巷的林宅已经回不去,李师师又与父母一刀两断,宁死不肯再回威远镖局。自己的住处秘密太多,暂时不好让她住进来,只好先留在太尉府。
不过有高俅在,李师师留在府中可以说是万无一失,比跟着程宗扬还安全。
程宗扬道:“不用担心,高衙内现在见我可亲热得紧。”
“哦?”
秦桧惊讶起来,“公子是如何做到的?”
程宗扬哈哈笑道:“我当着他的面掏出家伙,把一碗水吸得干干净净,他就拜了我当师傅。”
秦桧莞尔而笑,只当家主是说笑而已。不过家主一转眼就能把高衙内那个跋扈的小子收拾得服服帖帖,这分神出鬼没的手段连秦桧也不得不深感佩服。
“子元呢?”
“子元从凤凰岭脱身出来,还好伤势并不太重。”
秦桧顿了顿,“另外两位已经殉职。”
这仇连报都没地方报去。当时高俅知道内情,脸色也极不好看。
在太尉府的强力封锁下,凤凰岭的事并没有传扬开,外界只听说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因为执刀夜闯白虎堂,被军士擒获。高太尉仁慈为怀,斟酌再三,给了林冲一个“误闯”的罪名,免了他的死罪。
“云六爷到了吗?”
“已经到了梵天寺。公子出事,云六爷已经听说了,本来派了他身边最得力的几名护卫来助公子,被属下婉言谢绝了。”
“做得对。”
程宗扬道:“凤凰岭的事只是个意外,咱们真正的对头恐怕还没有出手,这个时候云六爷的安危比我们重要。备车!我这就上梵天寺!”
秦桧提醒道:“公子,此刻已是子时。”
“没关系,我想云六爷也不会见怪。”
云秀峰果然一夜未睡,一直在等程宗扬平安的消息。在梵天寺一处禅院中,程宗扬第一次见到这位云氏商会的当家人。
论年纪,云秀峰比云苍峰小了十几岁,两人的相貌却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他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袍,靴子、袜子也是平常的布鞋、布袜,若不是腰间悬的那块玉佩随时都能调动数万金铢的巨额财富,谁也看不出这个面带沧桑的中年人会是云氏的家主。
云秀峰的行踪遍及六朝,随身带的护卫足有上百人之多。一般商家的护卫大都是在外招募的武者,或者从晴州雇来的佣兵,云秀峰身边的这些护卫全都是云家的世仆,忠诚度全无可疑。
云家的护卫布置了明暗五重防护,将一座小小的禅院守得密不透风。除此之外,禅房外还有八名僧人分据四角,两两相对盘膝而坐,显然是梵天寺派出的守卫力量。
与道家的六大宗门不同,佛门的十方丛林更像一个松散联盟,属于十方丛林的寺庙行院远不只十座,其中也没有明显的层级划分。
梵天寺论规模尚不及近在咫尺的石佛寺,却是宋国十方丛林的核心。云秀峰入住梵天寺,也是向外界表明自己的实力。
夜已深,又赶了一天的路,云秀峰却没有丝毫倦意。他从头到脚打量程宗扬一遍,细致处连自己颈中那处奴隶烙痕也没有漏过,挑剔的眼神让程宗扬忍不住腹诽:大家又不是没见过,有必要这么认真吗?
“伤势如何?”
程宗扬摸了摸脑袋上的绷带,苦笑道:“无妄之灾,还好没把脑袋丢掉。”
“会留疤吗?”
程宗扬愕然片刻,“应该不会吧?伤得又不深……”
心里嘀咕道:连会不会留疤你都问,难道你想挑女婿?大小姐那脾气……还是免了吧。
终于,云秀峰露出满意的眼神,“坐。”
晋国的习俗是屈膝跪坐,云秀峰用的却是宋国惯用的座椅,反映出商人是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的群体这一事实。
程宗扬已经透过水镜术与云秀峰打过几次交道,知道他不喜欢说废话,当下也不客套,坐下来道:“下午的事已经弄明白了,动手的是宋国禁军,但目标不是我们。原因是禁军一名教头出事,我们正好去拜访过那位教头,受了牵连,现在误会已释,对生意不会有什么影响。”
听程宗扬说得笃定,云秀峰也放到一边。“如此便好。筠州之事孙益轩已经跟我说了,你处置得不错。”
程宗扬笑道:“幸好有孙兄帮忙,不然光筠州的地头蛇就够我头痛了。”
“没有云家帮忙,你一样能解决,”
云秀峰又道:“客气话不用多说。”
一名家仆送上茶来。云秀峰道:“三哥从南荒回来便对你赞不绝口。你在建康不过数月,就有拉链坊、水泥坊、丝织坊和临江楼诸事。云某原有心把你收入囊中,直到玄武湖一战方知程公子非是池中之物。”
“云六爷过奖了。”
云秀峰道:“临川王临阵退缩,若不是你从中穿针引线,我云家未必容易这么下台。”
这倒是实话,云家插手晋国宫闱之争,已经犯了大忌,即使能够脱身也免不了元气大伤。
云家与萧侯原本没有什么交情,但因为程宗扬的缘故,双方顺理成章地联手,才避免玄武湖一战后的清算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云家帮萧侯,也是在帮自己。
云秀峰道:“既然无法收入囊中,程公子又是可交之人,大伙不妨一同做番生意。”
“云六爷快人快语!”
程宗扬放下心来。虽然有云苍峰的照顾,与云家的合作中,一切决定都由他自己作主。
但程宗扬心里明白,自己手里所有的资金几乎都是由云家出借,说云家是自己的债主更准确一些。云秀峰这番话等于正式表明态度,认可自己是彼此平等的合作伙伴。
程宗扬心情大好,意气风发地说道——“那大家就谈谈做生意的事吧!”
“要谈的无非两件,云家能为你做些什么?你又能为云家做些什么?”
“好!先从眼前说起,如今最要紧的就是这笔战争财。”
程宗扬道:“贾师宪穷兵黩武,自己后院起火还要兴兵讨伐江州,现在已经是泥足深陷。不知有多少商家盯着宋国这块肥肉想赚上一笔,但多数人盯着的都是军械生意,云六爷这次来临安,也是为了军械吧?”
“不错。宋国急需一批精铁,云某为了这笔生意周旋数处,此间辛苦一言难尽。”
程宗扬拍手道:“正是如此!军械生意虽然利润丰厚,但大家都盯着这笔生意,做下来反而不易。宋国各地都有常平仓平抑粮价,再加上牵涉范围极广,表面上看,粮食生意是最不好做的,但真做起来反而不引人注目。更何况宋国的粮食只有我们能做,别人想做也做不来。”
程宗扬道:“做粮食生意,首先要有大笔资金,其次要有遍及各处的商号,这两项便堵住一般商家插手的路子。但如果只是这两点,宋国也尽有资本雄厚的大商会,再加上晴州那些钜商,未必弱于我们在宋国的影响力。”
云秀峰抚摸着腰间的玉佩。“我担心的正在此处。只怕我们辛辛苦苦,却给了别人做嫁衣。”
“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势——”
程宗扬从容道:“我这些天一直在看各地粮价,可以断定除了我们制造的波动以外,并没有其他商家插手宋国的粮食生意。为什么江州之战打了快三个月,直到现在也没有其他商家大举来倒卖粮食?”
程宗扬给出答案:“因为他们不知道战局如何。即使知道战局如何,也不知道战争会持续多久。也许今天刚大举买入粮食,明天江州之战就已经结束,巨额资金都打了水漂。所以我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:江州。”
程宗扬还有一半的话没有说出来:现在自己的优势又多了一个宋国的太尉府。
一个操控棋局两端的弈手还会在粮战中落败,简直没了天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