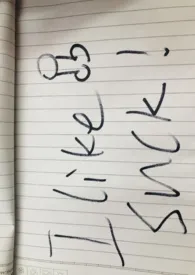这处宅邸两人来过,只不过当日跃入时,迎面撞上一群蹲着吃饽饽的光头,这次触目所及,没有了趾高气昂要跟自己辩经的信永方丈,只有遍地尸骸。
独孤谓倒抽了口凉气,“浑府这是……被人灭门了?”
铁中宝露头看了一眼,也不禁龇牙,“太狠了吧?一家老小都不放过?”
杜泉跃上墙头,蹲身扫视一圈,说道:“浑家三代高官,是长安城里有名的富户。多半是被贼人盯上,趁乱杀人越货。”
独孤谓摇头道:“未必是贼人下的手。”
铁中宝道:“为啥?”
“你看,浑家的家主双手反绑,咽喉中刀,蜷膝倒卧,并无挣扎痕迹。显然是被人捆绑带至此处,然后按住肩膀,引颈就戮。”
独孤谓指点着说道:“其他人等也是一般,周围的仆役,伤势多在后颈、后腰等处,应该是见主人被杀,仓皇逃奔,被人追上砍杀。若是被贼人破门抢掠,岂会如此?”
童贯也凑出头来,小声道:“难道是被官军灭的门?”
“不好说。”独孤谓道:“但若是官军奉命而来,应该会将其下狱,严加拷掠。行事如此仓促,倒像是私下所为。当然,也不排除贼人冒充官军,将其诱骗至此,再行杀戮。”
铁中宝道:“劫财就劫财,用得着把人都杀了吗?”
“老铁这话正说到断案的根本了。”独孤谓道:“凶手灭门的动机,究竟是劫财,还是另有其因?”
童贯道:“不是为财,难道还有别的缘故?”
程宗扬开口道:“浑家跟窥基有关连?”
信永等人当日断不会无缘无故躲在这里,还连饽饽都吃上了,杜泉道:“浑家这位家主,是窥基的记名弟子。”
童贯眼珠一转,“下手的是熟人!怕事后被揭穿,才要灭口!”
“哎,这位小公公,很机敏啊。”铁中宝道:“独孤郎,你能看得出来是谁干的不?”
独孤谓摇了摇头,“这哪里看得出来?除非过去仔细察验,找找凶手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。这种大案,真要查肯定能多少查出来些线索,只是没了苦主,未必有人去管。”
说着他心里泛起一丝酸辛,若论查案,六扇门的泉捕头比自己高明十倍,可惜伊人行迹全无,生死难测。
程宗扬凝视良久,然后冷冷道:“活该。”
浑家既然与窥基勾结,当日的血债,自然少不得他们一份,自己不报复回去就是好的,难道还要替他们找出凶手,讨个公道?
“不管了,走。”
众人离开浑宅,程宗扬折而向西。
独孤谓提醒道:“咱们那天没去过西边。”
“知道。”程宗扬道:“我去一趟上清观。”
独孤谓挠头不解,还是策马跟上。
上清观同样大门紧闭,此处是道门重地,倒没有贼寇过来骚扰。
童贯上前叩了叩门,尖着嗓子道:“汉国辅政大臣,宋国户部侍郎,佩汉宋两国使印,舞阳侯亲临造访!尔等速速启门相迎!”
院中的楼观上有人张望了一眼,随即观门大开,几名道士出来迎接。
程宗扬下马道:“我与赵道长相识已久,听说道长受了伤,过来探望。”
一名长须的道人稽首施礼,“有劳程侯探问,请进。”
程宗扬一边走一边随口攀谈道:“道长是长青宗门下?”
“不敢。贫道谭长元,出自太乙真宗。”
“哦?”程宗扬看了他一眼,“是哪位教御门下?”
“林之澜林教御。”
蔺采泉继任掌教之后,太乙真宗出奇的低调。
尤其是这回秋少君升为教御的大典,太乙真宗在各处的门人都应召返回龙池,没想到在这里还遇上一个。
自己跟太乙真宗打过的交道何止一二?
只不过跟自己来往的都是王哲、蔺采泉、秋少君,当然还有卓云君这样的高层,寻常门人全然不知自己与太乙真宗的渊源,只当自己是远来的贵客。
程宗扬没有露出什么异样,“赵道长伤势如何?”
“归真师兄被那些妖僧诡术所伤,眼下还在昏迷。”
“既然如此,我就不进去打扰了。独孤郎,取些礼物来。”
几名道人面面相觑,都不明白他这是弄得哪一出?
待见他脚步不停地径直去了后院,才略微有些头绪。
“燕仙师。”
程宗扬不过是打着探望赵归真的幌子来见燕姣然,他拱了拱手,“昨日宫中变故,可有扰到仙师?”
“有。”燕姣然用丝带扎紧袖口,正将调好的药膏揉成一枚枚龙眼大小的丸子,“昨日我原本应约往宫中,给贤妃诊脉,听闻事变,却是耽误了。”
程宗扬猝不及防,杨妃需要诊脉?诊什么脉?
燕姣然用一方雪白的巾帕抹净手指,“陛下尚无子嗣,难免挂怀。”
原来如此,李昂现在倒是不需要忧心子嗣了,毕竟老婆都没了……
程宗扬打了个哈哈,“城中乱象丛生,仙师有什么要帮忙的,尽管吩咐。”
“正好程侯亲自过来。这些宁心丸用花蜜炼制,最能滋阴安神,养血补气,禆益不足,程侯不妨带些回去。”
这是专门给赵飞燕准备的吧?
程宗扬大包大揽,“有多少?我全要了!”
燕姣然莞尔一笑,“承惠,一枚金铢一丸,共计二百四十丸。”
程宗扬摸了摸鼻子,苦笑道:“不便宜呢。”
一枚药丸两千铜铢,狮子大开口啊。
燕姣然笑道:“今冬酷寒,我有意备些药材,预防开春之后出现瘟疫。只是囊中乏金,只好将主意打到程侯头上,还请程侯莫怪。”
燕仙师把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,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?
就当是给赵飞燕肚子里面自己那个未出生的孩儿积福吧。
“做慈善这种好事,程某责无旁贷!这样吧,劳驾燕仙师给我备一千丸的,回头我让人把钱送来。”
燕姣然合掌施礼,“我代城中病幼,多谢程侯仁心。钱铢先不必送,待药丸炼好之后,我当亲手奉至府中。”
“燕仙师太客气了。”程宗扬这才说出来意,“惊理还好吗?”
惊理脸色虽然还有些发白,但比自己想像中的惨淡气色好了许多。
光明观堂的医术果然够强,断肢这种手术都处理得干净利落。
“主子。”惊理坐起身。
“别动。”程宗扬按住她的肩膀,然后朝她左腕看去。
惊理左腕光秃秃的,只剩下一圈仔细包扎好的纱布,再看不到手掌的痕迹,突兀得让人心痛。
惊理试图藏起断腕,被程宗扬小心拉住肘弯,“还痛吗?”
“不,不痛的。”惊理说着眼圈一红,“对不起主子,奴婢,奴婢已经是个废人……”
“说的什么话?”程宗扬道:“要不是你,被咬中的就是我了。”
程宗扬拉起她的手臂,在她断腕上一吻,笑道:“包得还挺好看。”
惊理破涕为笑,“好丑……”
“谁说的?有种特别的美,叫残缺美。有人就是喜欢这种的。”
燕姣然深深看了他一眼。
惊理唇角挑起,仿佛噙了蜜糖一样,“主子也喜欢吗?”
“呃……我可以欣赏。”程宗扬道:“我的女人,怎么样都是美的。”
惊理垂下泪来,“我还怕主子不要我了……”
“想什么呢?进了我程家的门,生是我程家的人,死是我程家的鬼!想跑?没门儿!”
程宗扬将她断腕贴在脸侧,笑道:“我小时候玩海盗游戏,把手藏在袖子里面,扎紧袖口,上面套个杯子,想像自己是一个手腕上装着钩子的海盗船长,带着手下纵横四海……”
惊理静静听着,脸颊越来越红,唇瓣娇艳欲滴,整个人都仿佛活过来一样,与方才苍白惨淡的气色迥然相异。
“小心。”燕姣然打断他们,“病人还需要休养。当心气血波动。”
程宗扬放开惊理,“你好好养着,不用担心家里。你紫妈妈也该回来了,到时候我来接你。”
“是,主子。”惊理依依不舍地应下。
燕姣然一边送他出去,一边道:“程侯出过海吗?”
“很可惜,还没有。”程宗扬道:“但听我内人说过海上的风云。”
“云家那位大小姐吗?”燕姣然微微一笑,“程侯是有福之人。”
“借仙师吉言。”程宗扬试探道:“我听小……乐姑娘说过,贵门与黑魔海有大比之约?”
燕姣然道:“程侯为何问及此事?”
“呵呵,”程宗扬干笑道:“我有点担心乐姑娘……”
燕姣然莞尔道:“明珠若想去,尚需一番努力。”
这就是说小香瓜修为不够,去了也是白送,看来光明观堂的人选八成还得落在潘姊儿身上。
“定好时间了吗?”
“有紫姑娘在,程侯何需再问他人?”
“紫丫头都不跟他们玩的,我也是怕她被蒙在鼓里。”
燕姣然道:“黑魔海已经失期年余,尚不知是否定下人选。”
光明观堂与黑魔海的大比,要等到黑魔海大祭之后,从巫毒二宗门人中选出天命侯,再与光明观堂的光明贞女一决生死。
如果人选被巫宗拿到,最后选出来的是西门庆,潘姊儿倒是能赶上给武大报仇。
如果最后胜出是毒宗,小紫对上潘姊儿,那场面……啧啧。
不知道双方的大比允不允许旁观?
燕姣然静静看着他,“程侯在想什么?”
在想怎么调教你们光明观堂的希望之星……
“想起路上遇到的事。我刚路过坊中的浑府,没想到一家人都被灭门,死者枕借……太惨了。”
燕姣然神色黯然,良久叹道:“医者医人,难医天下。悬壶济世,又能济得几人?”说着她抬起眼,“能救天下者,舍程侯其谁?”
程宗扬干笑道:“仙师太高看我了,我哪里救得了天下?”
“程侯可有拯救天下之志?”
程宗扬头摇得拨浪鼓一般,“没有!我能照顾好自己一家就不错了。”
“古人云:修齐治平。程侯能齐家,亦是佳事。”燕姣然合掌低首,“愿程侯居仁布德,常怀慈悲之心。”
程宗扬沉默移时,拱手告辞。
街上寒风依旧,程宗扬却感觉身上一阵燥热。
他解下大氅,放在鞍前,又卷起衣袖。
长安盗寇四起的乱象,浑府阖门被灭的惨状,都是因为李昂自己作死,是因为那些官员自私无能,是因为宦官的凶残和嚣张,是因为和尚们的贪婪和狂妄,跟自己有个屁的关系!
我也是受害人好不好!
可为什么自己心里如此烦躁?因为老贾出手乱局?
唐国朝廷烂成这样,老贾不出手难道就不乱了吗?
顶多是晚个一天半天,那些地痞迟早会发现金吾卫和各衙门无人当值。
即便是自己干的又如何?
就李昂干的那些破事,别说自己只是点了个火星,就算汉国为此光明正大的出兵,讨伐唐国无义,唐国也没脸说冤枉。
说来自己已经很克制了,除了干了李昂的宠妃,别的还干什么了吗?
说难听些,比起唐国被汉兵大军压境,百姓生灵涂炭,李昂拿一个杨妃把事摆平,别说他赚了,连唐国也赚大了!
燕姣然劝自己慈悲,自己哪里不慈悲了?
我都已经是滥好人加再世圣人了,难道还要我学佛祖割肉饲虎不成?
凭什么?
干!
长安城大街横平竖直,到处都是整齐划一的十字街,程宗扬却没有走直线,而是赌气一般,在城坊间东绕西转,有时深入暗巷,有时又绕到某处被抢掠过的庵堂、房舍。
众人都一头雾水,弄不清主公的意图。
他们一开始以为主公是忧心城中的乱象,出来察看局势。
到了大宁坊,临时起意,重走了一遍逃亡的路线,悼念死难的兄弟。
后来又去探望养伤的奴婢,也在情理之中。
可出了大宁坊之后,路线越来越奇怪,忽而向南,忽而往西,在各坊之间来回穿行,看行止,好像在寻觅什么,到了地方却又过门不入,一路上马不停蹄,似乎只是赶路。
不过主公板着脸,显然心绪不佳,众人都没有作声,只紧跟着主公马后,暗自握紧兵刃,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刺客。
这一路的见闻也让众人不禁悬心,昨晚的骚乱以抢掠为主,伤及人命的并不太多,然而这一路行来,所过之处几乎都有死伤,时不时便能遇到尸骸,令人不由得怀疑,昨晚的骚乱是不是被低估了?
日影将中,众人从一处坊门出来,迎面是一座雄伟的城门。
一阵错愕之后,众人才意识到,这一路东绕西转,竟然不知不觉到了皇城,眼前正是朱雀门。
皇城位于长安正北,朱雀大街尽头,与原本的大内太极宫连为一体,大内迁往大明宫后,各部的官衙仍留在此地,也是昨日事变中,杀戮最为惨重的区域之一。
大明宫内死者多是内侍、官吏、军士,皇城却聚集着大批来不及逃走的百姓商贩,都被神策军屠戮一空,死者数千人。
此时官吏逃散,军士弃守,偌大的皇城几乎空无一人。
朱雀门漫长而幽暗的门洞内血气扑鼻,虽然尸首已被清理,仍能看到满地血迹。
程宗扬勒住坐骑,游目四顾。
杜泉道:“那些内侍大概是巳时赶来,先闭了城门,然后纵兵砍杀。”他昨日正在皇城,亲历其事,说道:“我藏身檐上,直到傍晚才脱身。”
程宗扬道:“那些内侍为何要屠戮百姓?”
杜泉与独孤谓对视一眼,“那些军士可不是什么好鸟,抢劫杀人这种事,胆子大得很。”
“不光是神策军,宫中翊卫也有不少是长安本地的恶少。”独孤谓道:“白日当值,下值之后,杀人越货,无恶不作。”
程宗扬驻马片刻,然后穿过城门,左转往西行去。
沿着城墙西行,途中血迹处处,不时能看到掉落的鞋履,染血的幞头,还有掀翻的木轮车,打碎的酒瓮。
一直行到皇城西南隅,视野蓦然开阔。
青石铺成的街面尽头,是一片黄沙。
那片沙场宽及百步,场中寸草不生,唯独场边生着一株巨柳。
那株柳树大得惊人,此时绿叶凋尽,苍黑色的树身犹高十丈,数人合抱的树干上,分出无数巨臂般的枝桠,光秃秃的柳条低垂下来,笼罩在枝桠四周,如烟似雾。
远远望去,如同一座巍峨的云山,又像一个佝偻着身体的老迈巨人。
“这是独柳树,”杜泉指着北边道:“那边是为天下报功的大社。”
独孤谓道:“这里也是刑场,专门诛杀重臣大将之类的罪囚,以往叛乱的各镇节度使,被天兵讨伐捉拿,都是押赴京师,在此地处斩。”
程宗扬抬起头,视线沿着独柳树巨大的树身一直升到树梢。
烟云般的柳条无风而动,澎湃的死气潮水般涌来,浓郁得如有实质。
程宗扬闭上眼,丹田中的生死根不断鼓张,如同长鲸吸水,吞吐着此地不知郁积多少年的死亡气息。
他一开始只是想察看城中乱状,但从宣平坊出来,途中便陆续感应到一些死气,只不过间隔已久,大多数死气已经消散,只留下少许残痕。
想也知道,这样大规模的动乱,免不了出现杀戮和死亡。
直到路过大宁坊,死气蓦然变得鲜明而强烈。
程宗扬不想暴露自己生死根的秘密,按照当日的路线重走一遍,结果遇上浑府灭门的惨案。
丹田内的生死根仍然被那股诡异的寒气阻塞,转化不畅。
因此程宗扬又转往上清观,趁着探视惊理,一边用转化的生机助她恢复,一边顺便化解,却没想到临走之际,燕姣然会劝说他慈悲。
程宗扬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注入的生机太多,被燕姣然识破了生死根的秘密。
虽然王哲告诫过不要暴露自己身怀生死根,但即使被燕姣然发现,也不见得就有危险,毕竟王哲也没有因为自己身怀生死根就诛杀自己。
从燕姣然的反应看,也许有,但更大的可能是没有。
程宗扬最奇怪的是,作为与岳鸟人这个穿越者朝夕相处过的燕仙师,却认定自己并非天命之人。
程宗扬并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向谁证实自己的身份,他只是不明白燕姣然为何如此断定。
难道自己融入得这么成功,连燕仙师也把自己当成六朝土著?
不过燕姣然最后几句话,让程宗扬一时间出离愤怒,话中蕴藏的意味,就好像是指斥自己为了吸收死气,故意掀起杀戮。
我程大圣人是那种人吗?
我被李昂坑得这么狠,你怎么不出来主持公道,劝李昂善良呢?
那帮阉狗还在拷掠乱党,你怎么不去劝他们善良呢?
恼怒之余,程宗扬索性不再克制自己。
随后这一路,他倚仗生死根的感应,哪里有死气往哪里去,将沿途的死气一扫而空。
其实这会儿冷静下来,程宗扬能感觉到燕姣然不见得就觉察出自己生死根的秘密,最后那几句话,很可能是仅仅出于悲悯的好意,并非指斥自己冷血不仁。
反倒是自己胸中戾气太盛,有些过于敏感了。
但这一路走下来,却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意外:独柳树。
除了都卢难旦妖铃,程宗扬从来没有遇见过能够蕴藏死气的物品,更不用说是一棵植物。
这株独柳树不知经历过多少岁月,树下的黄沙场不知诛杀过多少高官显贵,自己甫一靠近,无数柳条便斜拂过来,积蓄的死气潮水般滚滚注入生死根。
让程宗扬意外的是,不知是漫长岁月的沉淀,还是独柳树本身的异状,汹涌而至的死气并没有像寻常死气那样,因为生死根运转不畅而凝滞,而是如同春雨一般,浸润着生死根,然后化为真元。
发现吸入独柳树的死气之后,生死根并没有堵塞,程宗扬闭上眼睛,双臂平伸,仿佛要去拥抱独柳树喷发出的汹涌死气一样,竭力催动丹田,将转化的真元纳入气海。
他进入第六级通幽境之后,气海扩大数倍,以往还算可观的死气顿时显得杯水车薪起来,更别说光靠自己修炼,想达到圆满的境地了。
可独柳树的死气仿佛无穷无尽,不过一刻钟,丹田就被浩荡的真元填满。
程宗扬敛神屏息,正待一鼓作气,突破通幽境初阶,踏入中阶的境界,突然间仿佛落下一道水闸,澎湃的死气戛然而止。
面前披拂飘舞的柳条低垂下来,宛如老君长垂的寿眉,接着一道柳枝摩擦般苍老的声音在心底响起。
“少……年……郎……”
“勿……多……食……”
程宗扬怔了半晌,这是什么鬼?谁在跟自己说话?柳树成精了?
他试探着在心里道:“你……是谁?”
心底波澜不起,自己刚才听到声音似乎只是一个错觉。
“前辈?”
“仙君?”
“大圣?”
“老树精?”
“柳爷?”
程宗扬把自己能想到的称呼全用了一遍,却不见任何回应,情急之下,张口道:“喂!”
郑宾、杜泉、童贯、铁中宝等人都在旁边,闻声同时上前,“程头儿?”
程宗扬回过神来,干笑道:“没什么,只是见这棵独柳树如此壮观,看得入神了。”
“京师就是好啊。”铁中宝道:“像我们凉州,哪儿见过这么大的树?早让人砍了当劈柴烧了。”
童贯道:“侯爷,这地方凉浸浸的,要不咱们回去吧。”
程宗扬呼了口气,“回去。”
他拨转马头,马蹄溅起黄沙,沿着来路驶去。
踏上长街时,程宗扬回头望去,只见一根柳条微微舞动着,仿佛在跟自己挥手告别。